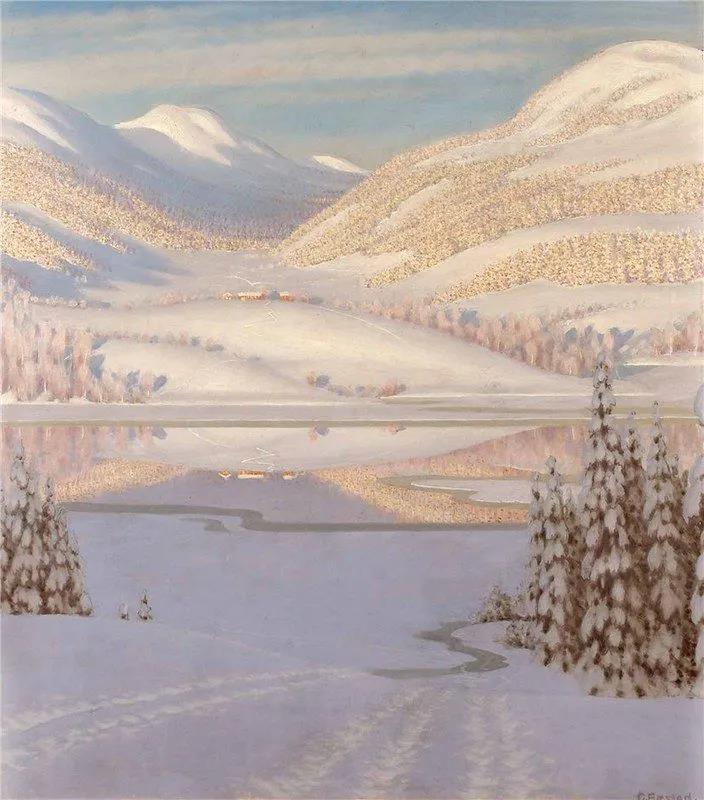
准确分析文本在翻译中的重要性
准确、简练、合逻辑一直以来都是法律的标签,在法律英语中也是一样的,法律英语翻译同样应讲求准确、简练、合逻辑。首先,用“法律”来举例子,英文上能够代表法律的单词很多,包括但不限于law;statute;act;code。
其中law的内涵较为广泛,既可以指代宏观上的法律体系,也可以指代具体的部门法,但其一般不用来作为某个特定法律命令的名称。
Statute专门指代以立法形式设立的制定法,是与判例法相对应的概念。
而act常用来作为单一法律的命名,如清洁水法Clean WaterAct、议会法Parliament Act,这里应注意,statute与act存在共用情况,而code不同于act,其用来指代法律的汇编,如联邦法规汇编Codeof Federal Regulation。
但在很多法律英语翻译实务中,翻译者并不区分这些词汇的用法,这给外语的理解带来了巨大的不便,尤其体现在中文译作英文的情况下。同时,译者还存在着漏译的情况,法律行文简练,条文中的每个词都对条文的理解至关重要,随意的漏译会使条文丧失完整性,继而影响对条文的理解。例如,arbitration clause一词应翻译为“仲裁条款”,而有些翻译人员受翻译中意译的影响,简单地将其翻译为“仲裁”,但实际上二者的意思并不相同,这也会给法律的理解带来困难,或许直接决定了一个仲裁案件的走向。除了漏译外,实务中也有部分翻译人员存在增译的现象,多表现为添加一些修饰性的文字,从而追求语言的优美。这些本来应属于翻译的技巧,但对法律而言可谓是画蛇添足,不仅不利于法律文本的简练,也不利于法律解释学的适用。
法理学上将世界的法系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法系,不同法系具有不同的法律文化,因而译者在理解法律术语时,必须将其放置于法律体系的大环境中予以理解。对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来说,双方存在如法律渊源、法律适用技术、诉讼程序、法律分类等差异,这些都可能会影响译者对法律术语的理解。
对于我国而言,在清末以前,我国一直是属于中华法系的国家,后来在引进西方法律的过程中,主要以大陆法系作为参照,因此虽然新中国成立后,我国也吸收了一些英美法系的内容,混合成了社会主义法系,但我国近代以来的法律因受德、日法律的影响,大陆法系的特征明显。这就造成了在对主要以英语为主的英美法系进行研究时,法律英语的翻译受法律文化影响较为严重。比如,对于assignment(of a contract)一词来说,其作名词的词义为“任务”“分配”,稍懂法律的人会将其翻译为“(合同的)转让”,但实际上该翻译并未考虑到法律文化的差异,“转让”的翻译不仅有失语义上的准确性,更会在实际研究中误导研究方向,致研究陷入困境。我们在理解assignment一词时,首先应了解到,在我国的合同法中,权利和义务是均可转让的。对于债务的转让而言,如果经债权人同意,则旧的债务人退出债务关系,由新债务人对债权人承担债务,当然我们在民法上称其为债务转移。而在普通法系的美国合同法中,虽然权利同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一样,是可以转让的,但义务是不可以转让的,只能转托。债务人把自己承担的合同义务转托给第三人(受托人)履行,并不能由此而解除自己对债权人承担的责任。美国合同法第二次重述中,也明确规定了义务的转托①。所以对于assignment,我们应该准确地翻译为权利的转让,对于义务,美国合同法中使用的是“delegation”,是指转托而非转让。如果未对权利和义务进行区分,而均翻译为“转让”,或者将义务的转托翻译为assignment of duty,会直接造成对法律的理解错误。由此也可看出,法律文化差异为法律英语翻译带来的问题,这应引起法律英语翻译人员的重视。



